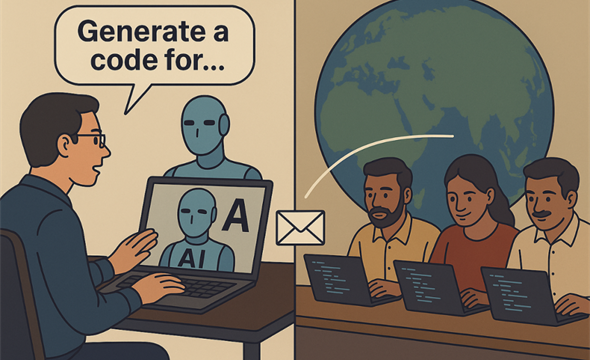文丨吴大郎
出品丨牛刀财经(niudaocaijing)
2021年10月7日,一纸法院判决书的披露,让旷视科技再次登上了各大财经新闻版面。
曾在旷视科技公司当司机的胡子健,以要将有公司敏感信息的录音出售给竞争对手相要挟,向公司董事局主席印奇索要人民币300万元。
印奇报警后,胡子健被抓,近日被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4年,胡子健对此认罪认罚。作为此案的受害者,印奇是近年来中国科技界和资本界颇受关注的明星人物。
2011年,旷视科技由三个年轻人正式创立,三位创始人是清华“姚班”毕业的印奇、唐文斌、杨沐。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月前的9月9日,科创板上市委员会通过旷视科技IPO申请,成为“AI四小龙”中第二家登陆科创板的公司。
早在2019年5月,旷视科技的估值已经超过40亿美元,那时刚刚完成D轮高达7.5亿美元融资,本次IPO,旷视科技计划募资60.18亿元。
一个人的命运,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对于企业,亦如此。
对于旷视科技来说,早在冲刺港股时人们就有些纳闷,一家质地优良的“独角兽”企业,创始人背景光鲜,有大佬加持,资本看好,为何上市之路一波三折?
官方给出的解释越少,外界的推测就越多。
例如在2019年10月,旷视科技被美国商务部列入了“实体清单”,登上这种清单的中国公司通常会面临各种硬件或者软件方面的技术干扰,进而可能会对未来业务预期造成影响。
尽管旷视科技很多核心技术在计算机视觉的算法层面,但这些算法所依托的高端GPU和特殊处理器供应有可能受限。
另一方面,在港股聆讯中,旷视科技也不断被监管机构要求回答更多问题,这让IPO初始申请最终在提交 6个月后进入“失效”状态,可能这些问题真的不是很容易解答。
有相关人士认为,大规模部署计算机视觉的商业模式可能存在侵犯隐私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中国香港地区以及在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要比在中国内地敏感得多等等因素。
当然,后来也有传闻旷视科技将以“H+A”股的方式登陆资本市场,这种方式固然流行,但前提是能先过其中一关再说。
作为AI独角兽,旷视科技在已经成立逾十年的节点上,自身造血能力依旧捉襟见肘让人对其高估值的合理性存在疑问。
尽管这类AI企业通常会在亏损中强调很大原因是因为优先股以公允价值计量导致的,所以公司在科创板招股书的财务报表中呈现的130亿元(4年报告期内)亏损并不能说明公司实际业务经营质量。
而报告期内,旷视科技扣除优先股公允价值变动(不含优先股相关的衍生金融工具)损失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分别为1.99亿元、5.32亿元、12.62亿元及 9.15亿元。
这种亏损额度和持续性,让什么“正处于发展期,需要大幅投入用于研究创新及市场开拓”等理由显得不充分,因为公司都要上市了,即便概念和潜力描绘得再好,但资本市场最关心的事情,并不是来看其烧钱能力的。
2017年-2020年三季度,旷视科技归母净亏损分别为7.75亿元、28亿元、66.4亿元和28.46亿元,累计亏损高达130亿元。
若将优先股以公允价值计量导致的账面亏损剔除,公司净亏损分别为2亿元、5.32亿元、12.62亿元和9.15亿元,最近三年及一期累计亏损仍接近30亿元。
高额的研发投入是公司持续亏损的一个主要因素。
报告期各期,旷视科技研发费用分别为2.02亿元、5.98亿元、9.33亿元和6.61亿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66.50%、70.02%、74.06%及92.23%。
要知道,AI科技公司在上市前都有个通病,就是都想把自己包装成概念高大上、生态系统强大、技术高端领先的形象,有时候会对投资者和审核人员造成很大的迷惑和干扰。
但拨开华丽的外衣,一家公司内核和务实赚钱的部分究竟怎么样,才是需要考察的重点。
旷视科技在招股书中将自身定位成一家聚焦物联网场景的世界级人工智能公司,面向消费物联网、城市物联网、供应链物联网三大核心场景提供经验证的行业解决方案。
说到这些场景,虽然说是“聚焦”,但其实这种概念塑造得仍然非常大,而具体到业务,旷视科技不得不涉足从系统层、算法、城市&供应链AIoT操作系统,乃至涉足传感器模组、终端与边缘设备、机器人与自动化装备等。
尽管公司自诞生以来不缺融资烧钱,但与扩大业务范围相对应的是精力的分散,很容易陷入什么都要做,而什么都难做到垂直行业最好的处境。
伴随着各个更垂直细分场景中诸多厂商的竞争加剧,旷视科技固有市场仍会不断被蚕食,如果技术壁垒不能转化成商业上的护城河,就会陷入比较尴尬的市场苦战。
从招股书来看,旷视科技的主营业务之中,城市物联网能占到总营收的65%左右,其次是消费物联网(包括SaaS和移动终端)合计约占到28%,供应链物联网目前不到8%,不过整体而言,公司的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50.96%、62.23%、42.55%及44.24%,毛利率水平已开始出现大幅缩水。
旷视科技虽然是成立了10年的AI独角兽,但相比海康、大华等老牌厂商,在渠道和商业议价能力上仍欠缺火候。2020年9月末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占流动资产的比重达到15.53%,坏账损失的风险较大,对经营业绩造成不良影响。
其实包括旷视科技在内,投资方和资本市场留给AI独角兽的耐性越来越少了。就如同人工智能被划分为五个关键阶段一样:技术触发期、期望膨胀期、幻觉破灭谷底期、启蒙爬升期和高原期。
目前的人工智能,就像是处在幻觉破灭谷底期,大家对其认识水平和评估深度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最初的新鲜与憧憬感早已不在。
近10年来,AI产业历经了从被热捧到快速“退烧”的商业变迁,而AI独角兽们自带的高研发投入和回报周期较长的特性,也让其持续盈利能力存疑,很多AI细分赛道也不会向移动互联网或者O2O一样出现明显的强整合趋势,烧钱留下的只是一片高企的融资总额和估值,成为烫手山芋。
尽管旷视科技创始人兼CEO印奇曾对外表示自己对上市其实没有那么在意,但谋求IPO,进一步打开稳定的融资渠道,是公司满足高额研发投入、保持市场长线竞争力所需的最好选择。
在如今这个阶段,历经数轮大额融资,其他风险投资对于接盘这个体量的公司需要十分斟酌,固有投资人也亟待退出,推动旷视科技快速IPO总有人比印奇更在意。
而对于旷视科技来说,登上“实体清单”导致去美国IPO势必面临各种刁难,冲刺港股遇挫之后,科创板才是最后的上岸选择。
但需要提醒的是,科创板需要对其给予更多“警惕”。